原创 刘先银经典点说《庄子》影子的影子《老子》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人生中,经验、洞见和知识才是真正的、永恒的祝愿,而幸福、愉悦和欢快是转瞬即逝的、虚幻的;人生的最后的华果是经验而不是幸福。
世界是我的表象——这是真理,适用于任何生活着的和认识着的生物,不过只有人才能够将其纳入反省的、抽象的意识之中。倘若人真的这么做了,他就会出现关于哲学的思考。由此,他会明确地认识到,他不认识什么太阳、地球,而永远只承认眼睛,因为太阳为眼睛所见;永远只承认手,是手感知了地球;就会懂得,围绕在他身边的这个世界只是作为表象而存在着的;即是说,世界的存在完全是就它对另一事物——一个进行“表象者”的关系而言的。人,就是这个进行“表象者”。“不仁”和“仁”构成一个认知整体,两个方面的内涵都认识到、把握到,你对事物的认识才能算是整体认知或全面认知。否则就只能算是片面或局部认知。 美和恶构成一个认知整体;善和不善构成一个认知整体;无为和无不为构成一个整体;言和不言也是一个整体;恃和不恃、居和弗居也是一个整体;还有“有无”、难易、高下、音声、前后、长短等都构成一个思想认知整体。 两个方面都认识到,没有遗漏,就叫作人类“思想认知”的整体性或全面性。 人类的思想认知拥有这个特性。 如果你看不到事物的整体,看不到事物的长短两面、难易两面,那么你对人或事物的看法,就一定是不全面的,一定是片面的,是有遗漏的,是无法真正用于指导实践的。 如果把“仁爱”当作一个独立的事物去看待,那么它必然包含仁和不仁这两个方面的内涵。
这一真理并非新得出的结论,笛卡儿所凭借的怀疑论观点中就已经包含了它,只不过贝克莱则是第一个断然将其说出来的人。虽然他的哲学观点的其他部分站不住脚,但就这一点而言,他为哲学所作出的贡献不容小视。我们只是从作为表象的一面来考察这个世界。这一考察虽无损于其为真理,但终究还是不全面的,也是由某种任意的抽象作用引发的,它凸显了人们内心的矛盾,并且以这一矛盾去假定世界为其表象,而他从此也再不能摆脱这一假定。不过,这一考察的片面性可以通过下面一篇得到充实,由另一真理来补充。但这一真理并不像我们此处凭借的那一个那般直接明了,而需通过更深入的探讨、更艰难的抽象与“别异综同”的功夫才可能达到。它一定是严肃的,对每个人而言,即使不是可怕的,也必然是不容忽视的。这另一个真理就是:每个人,他自己也能说且必须说:“世界是我的意志。”
主体就是,认识一切而又不为任何事物所认识的东西。物物而不物于物。因而主体就是这个世界的支柱,一贯被所有现象和客体作为前提的条件;原本凡是存在着的,即是对主体的存在。任何人都可能发现这一点: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主体,但仅限于它在认识着的时刻,当它作为被认识的客体时则不会这样。人的身体既然已经是客体,从这一点观之,也得称其为表象。尽管身体是直接客体,但终归是诸多客体中的一分子,并不能脱离客体的那些规律。与那些直观的客体一样,身体也同样在时间和空间里,在一切认识所共有的那些形式当中。正是因为这些形式,进而才有了杂多性。
因此,作为表象的世界——我们在此方面考察的这个世界,有着本质的、必然的、不可分割的两个半面——客体和主体。客体的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杂多性即是通过这些来表现的。主体却不在空间和时间里,因为在任何一个进行表象的生物中,主体都是完整的、未被分裂的。因而无论是这些生物里单独的一个客体,还是现有的亿万个生物与客体,都同样一道完备地构成这作为表象的世界;一个单独的生物消失了,其作为表象的世界同样跟着消失了。所以这是不可分割的两个半面;甚至对思想也是这样,因为任何一个半面的意义和存在都只能通过另一个半面来体现:共存共亡。二者又互为界限,客体的开始即是主体的终止。这是双方共同的界限,这也同样体现在下列的事实中:一切客体所具有的本质而普遍的那些形式——时间、空间和因果性,不用认识客体本身,只从主体出发就能够发现,能够充分地认识;就像康德说的,这些形式已先验地在我们的意识中。康德发现了这一点,这是他主要的功绩。现在我再进一步地说明,根据律就是我们先天所意识到的,客体所具备的一切形式的共同表述。由此可知,我们先天知道的正是这一定律的内容,别无其他。事实上,这一定律都已经把我们先天明确的“认识”说尽了——这便是由此产生出的结果。
对于我们而言,直观表象和抽象表象间的区别就是一切表象中的主要区别。后者只构成表象的一个类别,即概念——这也只是地球上的人类所专有。这区别于动物且达到概念的能力,即被称为理性。在此我们单就直观的表象展开论述,以后再考察这种抽象的表象。直观表象包含整个可见的世界或者说全部经验以及经验可能达成的条件。这是康德十分重要的一个发现——前面已经提到,他的意思就是:经验的这些条件和形式即是世界的知觉中最普遍的事物,世上的一切现象存在于一种方式共有的东西——时间和空间,当单独离开它们的内容时,不仅能够被抽象地思维,还可被直观。而这种直观并非是从什么经验的重复假借得来的幻象,而是毫不依赖任何经验,甚至会设想经验反过来依赖这直观;这是因为空间和时间的一些属性——比如直观先验所认识到的,都能够作为一切可能的经验的规律;不管在哪里,经验都须遵照这些规律而取得效果。我曾在讨论根据律的那篇论文里将时间和空间——倘若它们是纯粹而毫无内容地被直观的——看成隶属于表象的、特殊而单独存在的一个类。
但如果将时间和空间分开单独来审视,即便令其没有物质,也还能够直观地加以表象;然而物质就不能没有这两者。物质与其形状是不能分割的,是形状的就必以空间为前提条件。而物质的全部存在也不可能游离于其作用之外,作用总是变化的,且只是在某个时间里的规定。但时间和空间并非分割开来作为物质的前提,物质的本质是由二者的统一构成的;正因为这样,如上所述,其本质是存于作用和因果性中的。倘若所有能够想到的现象和情况,可以在无限的空间里排列而不致拥挤,或是在无尽的时间里先后继起而不致紊乱,那么,在这种现象和情况之间就没什么必然的关系可言了。而依据这些关系对这些现象和情况所作的规则就更无必要,或者说没法得到应用了。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虽然空间中有一切的并列,时间中有一切的变化,但只要这两者各自独立,而没有在相互的关系中有其过程和实质,因果性就无从谈起;而物质真正本质的构成又离不开这因果性,由此可知,没有因果性,就没有物质。但因果律获得意义和必然性的原因在于变化的本质不仅仅是情况本身的变化,更是空间中同一地点上情况随时间的变化,即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情况;是同一特定时间上情况随空间的变化,也就是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的情况。二者只有这样相互地制约,才能使照此变化的规则具有意义且具必然性。因而,因果律所规定的不是只在时间中的情况相继起,而是就一特定空间而言的;情况的存在不是在一特定的地点,而是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变化即是依此因果律发生的变更,每次都会同时且统一地涉及到空间和时间的某个部分。由于因果性,空间和时间才得到了统一。
虽然直观须经由因果性的认识而成立,但就此以为客体与主体间存在着原因和效果的关系,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这一关系只存在于直接的和间接的客体间。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的误解,才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有关外在世界的实在性的愚蠢争论,在争论中才会出现独断论与怀疑论相互对峙的情况;前者一会儿是实在论,一会儿又是唯心论。在此要对争论双方说明的是:首先,客体就是表象;其次,它的作用就是能够直观的客体的存在,在其作用下,事物的现实性随即产生;但想要不同于其作用,在主体的表象之外实现客体的实际存在,要求真实事物有一个存在,那是毫无意义并相互矛盾的。所以只要直观的客体是客体——表象,那么,认识了直观客体的作用方式即是完全认识了这一客体,除此之外,就再没有什么是为这认识而留存于客体上的了。就此而言,存于空间和时间里的直观世界,纯粹通过因果性实现自身,因而也就是实在的,它即为它显现的东西,且完整而毫无保留地作为表象,按因果律而联系着。这即是它经验的实在性。另一方面,一切因果性又只对悟性而存在;因而整个现实的世界——发生作用的世界总以悟性为条件;倘若没有此条件,这样的世界毫无意义。但不仅仅是为这,而是因为想象一个不存在主体的客体根本就不可能不是矛盾的,所以我们才会否认独断论所宣称的那种在主体之外的实在性。表象就是整个客体的世界,无可移易,因而只能以主体为条件,这也就意味着其具有先验的观念性,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切是假象。它是什么就显现出什么,即显现出一连串的表象,根据律就是穿起这一系列表象的韧带。对于具有健全的悟性的人而言,这样的世界——即便从这世界最内在的意义上讲,也是能够理解的,对悟性而言,这是完全清晰的语言。
就如同从太阳的直射之下走进月光间接反射的光里一般,我们现在探讨的角度就是从直观的、当下的、自为代表和保证的表象转向了反省的思维,理性而抽象的、推理的概念。概念从直观认识中来,只有在这种认识的关系中才显现它的全部内容。倘若我们总是纯粹直观地行事,那么一切都会是稳固而明晰的,没有问题,没有怀疑,没有谬误;人们不会有什么要求,也不能有要求;在直观中人们满足于当下已有的。直观是其本身所具有的,因而凡是纯直观所产生的、忠实于直观的事物——比如真正的艺术品,就不可能是错的,也不会成为某个时代的遗弃物,因为它并不发表某种意见,而只是事情本身的呈现。而在理论上,随同抽象的认识和理性就会出现怀疑和谬误,在实践中产生顾虑与懊悔。在直观的表象中,事实会被假象在当下瞬间歪曲;在抽象的表象中,谬误能够支配几十个世纪,给整个民族套上它牢固的枷锁,能够扼杀人类最至高无上的冲动;它的奴隶们——那些被它所蒙蔽的人们,甚至会给那些不受蒙蔽的人带上镣铐。对于这样的敌人,历代先哲们不知与它进行过多少次实力悬殊的斗争,最后从它那里缴获的一点东西才被珍为人类的财富。我们一踏入这敌人所属的领地对它的警惕之心即刻就被唤起了,这是有好处的。尽管曾有人说,就算看不到什么好处,也不会放弃对真理的追求。这是因为,真理的好处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并且隔上某段时期又会意外地重新显现——在这里我还要说明一点:即便没有看到害处,人们也须去揭露并尽力铲除谬误,谬误的害处同样也是间接的,会在人们掉以轻心的时候又出现;且无论是什么谬误,都会藏有毒素。倘若令人类成为地球主宰的是人的智力和人的知识,那么就不会有无害的谬误;倘若是那些尊严而神圣的谬误,就更不可能是无害的了。为了对那些在某一场合某一地点与谬误做过崇高而艰巨的斗争且献出力量和生命的人表示些安慰,我不禁要插上一句:在真理还没有出现之前,谬误就如同猫头鹰和蝙蝠在夜里逍遥自在一般,固然还能嚣张一段时间,倘若说真理即便已经被认识且能够明晰而完整地被表达出来之后,还会再度被逐退,而旧的谬误又一次大肆重新占领它那片阵地,那么就如同说猫头鹰和蝙蝠会把东升的太阳吓回去一样。真理的力量就是这样,其胜利固然是来之不易,但足以弥补这个遗憾的是:一旦真理赢得了这胜利,是永远不会被夺走的。
直到这里为止,作为我们考察对象的表象,按照它们的构成分析,要是从客体方面入手,能够还原成时间、空间以及物质;要是从主体方面入手,则能够还原成纯感性和悟性(即所谓因果性的认识)。除去这两方面的表象,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中,只有人类还具有一种不同的认识能力,进而发起一种全新的意识。这就是被人们以一种冥悟的准确性很恰当地称为反省思维的意识。的确,这种意识是一种反照,从直观认识被引申出来;但是它的性质与构成完全不同于直观认识,属于直观认识的那些形式,它全然不知;即便是支配所有客体的根据律,在这里也呈现出另一种不同的形态。这全新的、能力更强的意识——所有直观事物抽象的反照,理性的非直观概念中的反照——人类的思考力即从它而来。人类意识与动物意识的区别即在于此。正因为这一区别,人类在地球上的行为才会与那些无理性的兄弟种属们有所不同,在势力上超过它们,在痛苦上也同比程度地超过它们。它们只活在当下,而人可以同时生活于过去和未来。它们只满足于眼前的需求,而人则以自身的机巧开始未雨绸缪,甚至还未出世的后代也受到恩泽。动物只能任由眼前印象的摆布,任由直观动机的作用摆布,而规定人的却是不受眼前束缚的抽象概念。因而人可以执行预先的计划,可按章程条款来行事,而不顾(临时的)环境、眼前偶然的印象。举个例子,人可以不动声色地为自己的死作出安排,能够伪装得令人毫无察觉,把自己所有的秘密悄然带进坟墓。不仅如此,在众多的动机里他还保留着真正的选择权。这是因为,这些动机只有在抽象中同时并列于意识当中,才会产生这样的认识:既然动机相互排斥,就只能在支配意志的实力上一决高下。占据优势的动机即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动机——这是通过考虑后的意志抉择,这一动机便是透露意志本性的可靠标志。而动物则相反,它们由眼前印象决定;只有它们对眼前的强制力产生畏惧了,才会抑制自己的欲求,直到这一畏惧成为习惯时才会受到约束,这即是对动物的一种训练。动物也有直观、有感受;而人除此之外则还需要思维,需要知道;欲求是两者都有的。动物通过姿态与声音来表达感觉与情绪,而人传达思想或隐瞒思想则靠语言。可以说语言是人类理性的首要产物、必备工具。因而语言在希腊文与意大利文中,与理性用同一个词来表示:在希腊文中是“逻戈斯”,意大利文是“迪斯戈尔索”。德语里的理性(费尔窿夫特)Vernunft一词是从“理会”(费尔涅门)Vernehmen衍生而来的,但与“听到”Horen并不是同义词,有种理解语言所表达的思想的意思。没有语言的帮助,理性难以完成它那些最重要的使命,像众人协作一致的行动,几千人按照计划的合作;比如文明、国家,以及科学、以往经验的保存、将共同的事物概括于同一概念的真理的传达、谬误的散布、思想和作诗、信条与迷信等等,诸如此类。只有在死亡中动物才会认识到死亡,而人则有意识地渐渐走向死亡;即便有人还没有意识到生命即是在不断的毁灭中逐渐走向死亡,在某一个时刻他仍会产生对生命的焦虑。而人之所以会有不同的哲学与宗教,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概念是表象的特殊类别之一,在种类上,和我们前面所考察的直观表象全然不同,它只会出现在人的心智中,所以有关概念的本质,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获得直观而真正明白的认识,只可能是一种抽象的,推理的认识。
概念与直观表象,尽管两者有根本的区别,但概念对直观表象又有一种必然关系,失去了这一关系,就无所谓概念了。因而这一关系就是概念的全部内涵和实际存在。反省思维即是直观世界的摹写和复制——尽管这种摹写十分特别,所用的材料也全然不同。所以把概念称为“表象之表象”,再恰当不过。
根据上面的叙述,又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概念是抽象的表象,所以并不是十分确定的表象。由此每一项概念便有了人们称为意义范围或适用限定的东西——不管这一概念是否只有一个适用的实在客体场合。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它们的某些共同之处:在某一概念里被思维的部分,同时又会是另一概念里被思维的部分;反过来也一样;尽管两者同时,却又是真正不同的两个概念,这两者,或者是至少两者中的一个又有着另一概念所不包含的东西。每一个主语与其谓语就包含在这样的关系里,对这一关系的认识即是“判断”。
理性只在有所取之后才会有所与,仅就其本身而言,除了用于施展的空洞形式而外,它一无所有。整体上而言,逻辑还可以算是纯理性的科学。
在其他科学中,理性接受了源自直观表象的内容:这内容在数学中来自先于经验、直观意识着的空间关系与时间关系;纯自然科学中——我们对于自然过程先于经验的那部分知识之中,科学的内容源于纯粹的悟性,源于因果律及其结合时间、空间的纯粹直观的先验认识。除此而外的科学——一切不是从上述来源中获得内容的科学,都源于经验。所谓的“知”就是:在人心智的作用下有某种可以任意复制的判断,在这些判断之外的事物中也含有其充足的认识根据,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判断不是假的。因而“知”是抽象的认识,并以理性为条件。尽管动物也有直观认识,它们做梦这一点也可以证明其存在对直观认识的记忆,有记忆当然就会有想象,但严格说来,这并不能说明动物也有所“知”。所谓的动物意识,指的是意识作用这一概念,从语源上来说虽是从“知”而来,但却和表象作用这概念——不管是哪种表象作用——是一致的。所以才会说植物虽然有生命,但没有意识。“知”是抽象的意识,是将在其他方式下认识的一切在理性概念中固定下来的作用。
由此说来,从寻找整个世界的一个有效因或目的因出发的哲学是不可能的,我的哲学就不问世界的来由,不问为什么会有这个世界,而只对这个世界是什么感兴趣。注意,“为什么”是低于“是什么”的,“为什么”源于世界现象的形式和根据律,且只在这一范围内有意义和妥当性,因而早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了。当然,人们也可以说“世界是什么”,这一问题无须帮助就能够认识到,人自身就是认识的主体,而世界则是这一主体的表象。这一认识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的,但只是直观而具体的认识,倘若在抽象中复制这些认识,将先后出现且变动不居的直观,将这个广泛概念包括的东西,将只是消极规定的具象而模糊的知识上升为一种抽象而明晰的知识,这些才可称为哲学的任务。所以哲学应是有关整个世界本质的一个抽象概括:既有关世界的全部,又相关一切的部分。
所以,是否在哲学问题上有天分,就看柏拉图所确定的一条:在部分中认清统一,在统一中看清部分。由此哲学就是极普遍判断的总和,完整性中的世界本身就是它的认识依据,没有半点遗漏,即人的意识中所呈现出来的所有。哲学则是世界在抽象概念里的完整复制,就如同镜子里的反映。因为本质上的同一,这些抽象概念合为一个概念,相异的分为另一概念。哲学的这一任务早已被培根所安排:“忠实地复述这世界本身的声音,世界规定了多少,就说出多少;只是这世界的阴影与反映,毫不掺杂自己的东西,仅是复述与回声——这,才是真的哲学。”(《关于广义的科学》)我们之所以承认这一点,是基于培根当时还未能想到的一种更广泛的意义。
 刘先银题写书名:大公无私
刘先银题写书名:大公无私
 刘先银题写书名:一念之慈,万物皆善
刘先银题写书名:一念之慈,万物皆善
 刘先银题写书名:觉醒年代
刘先银题写书名:觉醒年代
 刘先银题写书名:问道,注目礼
刘先银题写书名:问道,注目礼
影子的影子叫魍魉:刘先银经典点说影子的影子,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刘先银经典点说《庄子》影子的影子《老子》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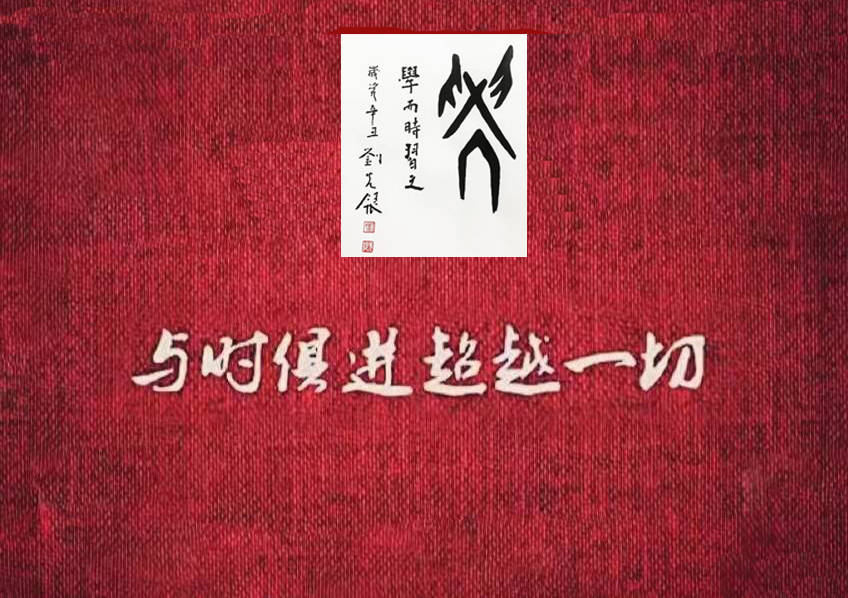 刘先银题写书名:学,学而时习之
刘先银题写书名:学,学而时习之
庄子《齐物论》最后一段讲了一段影子与影子的影子的对话。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释文】影子的影子魍魉,问影子说:“我刚才看到你在走路,现在又看到你停了下来。刚才看到你是坐着的,现在你又站起来了。我怎么看你没有一点点的主见和操守呢?”影子说:我是有自己的主人的,所以才会这样没有主见。我的主人也有主人,我的主人也是这样的,你叫我如何能做到有主见。我们就像蛇身上蜕下的皮寒蝉的翅膀都是受控制的。所以说我们又哪里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又哪里知道为什么不这样?”
这里其实是说万物都是相互依赖的。世人皆命有所制,浊苦一生,却不知悲从何来。真正的超脱就是无所待。我们都是受到外在的人和事的影响,如果你只相信你看到的一切,那么你一定会受制于人,一切的行动都受外在力量的驱使,我们会把它误解为命运,去感概命运难以改变,好像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必然的。其实这都是因为我们在使用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一直相信我们看到的一切,囿于我们的认知,所以才会有这种宿命论。影子的影子魍魉只能看到影子,而看不到影子的主人的存在。我们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却又看不到影子的影子。这是一种认知隔离,我们都是局限于相应的时空,受限于一定的时空范围。影子和魍魉都是受制于外,都是心智在动的结果。而我们的心神我们的本我是无为的,这时才能打破时空的束缚。
从另一个角度解读,我们头脑中各种念头和声音就是魍魉,有评判我们的、责备我们的、赞美我们的,就像魍魉在责备影子无特操与,影子就是我们对外在环境的反应。如果知道魍魉和影子都不是那个根本,我们的心头就再没有任何挂碍了,再没有任何观念声音能干扰到我了,这就是一念无我,超凡入圣。反之,这个魍魉的声音会始终在我们脑海中回响,会责骂我们评判我们嘲笑我们。然而,魍魉的根本还是我的心中之物,是我心中有那个念头,才会产生魍魉这种干扰的声音。所以,我们要回归我们的本心,那颗光亮的本心,一尘不染的本心,而不是在世俗的评判中去寻找自我。庄子说,吾所谓无情者,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精神的世界,不需要我们刻意的去求得圆满,只要我们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精神世界自然会饱满起来。
其实我们一直活在魍魉的影响下,活在头脑编织的虚幻中,不由自主就被它牵着鼻子走而陷入喜怒哀乐而不自知。
一大早小王去领导办公室交自己的工作汇报,领导摆着一张脸不耐烦的说:“放那儿吧,我有空再看。”于是小王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一会儿在想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到位,一会儿在想领导是不是对自己很不满意,一会儿又觉得自己很差劲,一会儿又考虑是不是要换个工作等等,一天都陷于焦虑不安的状况中,临下班时领导过来跟她说:“工作汇报我看了,做得不错,再接再厉。”此时小王才如释重负,安下心来。
实际上领导那时刚好被其他部门的事情恼火,刚好被小王撞上了,小王于是就对号入座了,一整天被头脑编织的虚幻谎言给蒙蔽了。
越是在意别人看法的人越容易被困在这样的烦恼中不可自拔。别人无心的一句话都会去无限放大,这都是我们的感官认知障碍带来的无明烦恼。
我们每天从开始睁开双眼的那一刻起就被外物牵着走了,迷失自己了,虽醒犹梦,晚上睡着是夜晚梦,白天是白日梦,这叫颠倒梦想。
我们不光被自己骗,也被他人骗被环境骗。当有人在我们面前说某人的不是,我们很容易就对此人有了偏见,即便我们并不了解他。尤其是父母当着孩子的面经常说另一半的坏话是极其不妥的,这会给孩子心里埋下怨恨的种子而影响其一生。
商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利用各种人性的弱点迷惑消费者,人们莫名其妙的就会上钩乖乖掏钱。
还有各种诈骗层出不穷,这都是人被感官认知障碍蒙蔽了双眼导致的。
以上这些还只是假相中的假相,实际我们生活的这个以感官认知的世界本质上全是虚幻不实的,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触摸到的都不是事物的真相,我们认为的真相只是头脑以假为真而已。
真相只有在停止感官认知的时候自然呈现,真相无法由大脑推理获得,因为人的感官认知是有局限性的,只能看到事物的表象而作出判断,真相在看不到听不到的地方。
管知止而神欲行,我们唯有让这颗一直沉迷于外部五光十色的虚幻世界里的心收回来并清静下来,让心主神明,我们才能够看清一切。
当湖水被风吹过,动荡的湖水卷起湖底各种泥沙而变得混浊,当风平浪静的时候,湖水开始清静下来,所有的泥沙沉入湖底,湖水变得清澈明净,就像明镜般可以映照万物。
我们的心就如同湖水,当我们的心在感官认知的作用下被外物牵动而动荡不安,变化无常,不得清静,一旦清静下来了,即刻心如明镜,天地可鉴。
当我们回归自性,心主神明的时候,一切都是觉知,直觉,就不会被困在头脑各种加工编织的虚幻中而苦不堪言。
刘先银:庄子《逍遥游》中曾说,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
庄子《逍遥游》中曾说,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这是我国古代书籍中对于长寿之人最著名的描写了,但我们都清楚长寿之人也不能突破身体的极限,庄子描写的长寿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而真实的长寿者,我国也是有很多的。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49
五色令人目盲(五色的缤纷会令人眼花缭乱);
五音令人耳聋(五音的纷杂会令人听觉不敏);
五味令人口爽(五味的珍馐美馔会令人舌不知味);
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纵情狩猎会令人心放荡);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难得之货令人图谋不轨)。
是以圣人(因此有道的圣人),
为腹不为目(但求安饱不注重眼花缭乱的诱惑),
故去彼取此(所以要去掉有害的念头,选取有益的德行)。
【解析】天下本无事,随处皆自在。当你被过去的故事所纠缠、被未来的故事所惊摄、被现在的故事所羁绊时,相应地,静下来去倾听或自己亲自呼吸冥想。就像大地吸收雨点一样,就像药片溶解在水里被你饮下一样。竭你所能,让自己感觉自在、平和。
未曾生我谁是我?
生我之时我是谁?
我死之后我是谁?
无我之时这世界还在吗?
看看这个世界,富人是怎么保证自己生生世世不会沦为穷人?不过是不经心地指尖一触,不过是无意识地漠然点击,当娱乐大量占用人们的时间,让人们丧失思考的能力,社会麻醉剂将会带来沉迷的人继续沉迷,清醒的人保持清醒,人与人的差距,甚至阶层间的差距也就来了。只需要像喂婴儿奶嘴一样,为穷人安于现状提供源源不断的娱乐就行了。反思一下现实的现象:当你想认认真真做一件事的时候,总会有各种因素干扰你。其实这些都是“多巴胺陷阱”。多巴胺是一种神经质,它能够给人带来即时的爽感。但同时,它又像一款廉价的毒药,让你在快乐中不断沉沦。相反,内啡肽需要人克服本能,才能艰难获得。但一旦拥有,你就会享受到自我提升的巨大满足。这个社会最残忍之处在于,穷人都沉浸在多巴胺的爽感中;而富人,却在逼自己追逐内啡肽。
我是谁?
时间是什么?
真实的人物、理性的思想、逻辑的言辞、智慧的对话。老子把心理治疗、历史人物、时尚叙事结合起来,用哲理的形式加以展现,完全可以把它当成现代人的心灵疗愈故事。
五色、五音、五味,游荡其中唏嘘不已。
